五、圆满
对我们来说,对灵性东方的愈发熟识仅仅象征性地表达了一个事实,即我们正在开始与我们内心之中仍然陌生的东西发生联系。否认我们自身的历史前提是愚不可及的,那将是再次失去依靠的最佳手段。只有牢牢站在自己的土地上,我们才能吸收东方的精神。
古德云:“世人舍本逐末”。这句话针对的是那些不知道神秘力量的真正源泉何在的人。东方的精神产生于黄土地,我们的精神也只能产生于并且应该产生于我们自己的土地。因此,我以一种常被指责为“心理主义”的方式来切入这些问题。如果它指的是“心理学”,我将感到很荣幸,因为我的目的正是要把所有神秘学说的玄学论断毫不留情地推到一边,因为语词的这种秘密的权力动机(Machtabsichten)与我们的极度无知非常一致,对此我们应当谦虚地承认。我坚决要把听起来有玄学意味的东西暴露在心理学认识的阳光之下,并且尽力阻止公众相信那些令人费解的断言(Machtwörter)。坚定的基督徒可以坚信下去,因为那是他所承担的责任,但非基督徒已经丧失了信仰的恩典。(也许他从出生起就已经遭到诅咒,不能信仰而只能去认识。)因此,他没有权利相信其他任何东西。玄学把握不了任何东西,但心理学却可以。因此,我会剥去事物的玄学外衣,使之成为心理学的对象。这样一来,我至少可以从中得到某种可以理解的东西并且为我所用。不仅如此,我还从中了解了此前我无法理解的、隐藏在象征背后的心理状况和过程。但由此我也能走上类似的道路,获得类似的体验,倘若最后仍然有某种无法言说的玄学的东西藏在背后,那么它将有最好的机会显示自己。
我对伟大东方哲人的赞叹与我对其玄学的不敬同样无可置疑。 注40 我怀疑他们是象征主义心理学家,最大的错误莫过于按照字面去理解他们。如果他们说的真是玄学,那么理解他们将毫无希望,但如果他们说的是心理学,那么我们不仅能够理解他们,而且能极大地从中受益,因为那样一来,所谓的“玄学”就是可经验的了。如果我相信有一个绝对的神,他超越于一切人类经验,那么我不会对他感兴趣,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但如果我知道,神是我灵魂中的一种强大冲动,那么我就必定会关心他,因为那样一来,他将变得和现实中的所有事物一样极为平常,变成重要而实际的东西。
“心理主义”的骂名只适用于那些自认为可以完全掌握自己心灵或灵魂的愚人,这样的愚人实在太多了;虽然我们知道怎样对“心灵”夸夸其谈,但是对心灵事物的贬低仍然是一种典型的西方偏见。如果我使用“自主心灵情结”这一概念,大家会立即产生一个偏见:“只不过是一个心灵情结罢了”。我们为何能够如此确定心灵“只不过是”呢?我们仿佛根本不知道,要么就是一再忘记,我们所意识到的一切都是相(Bild),相就是心灵。那些认为把上帝看成心灵的推动者或被推动者[即自主情结]就是贬低了上帝的人会受到无法控制的情感和神经官能症状态的折磨,他的意志和整个生活智慧将会一败涂地,这是否证明了心灵的无能呢?当埃克哈特大师说“必须让上帝在心灵中一次次再生”时,他也该被指责为“心理主义”吗?我认为,应当拿“心理主义”去指责这样一种理智,该理智否认自主情结的真正本质,并想按照理性的方式把它解释为已知事实的结果,亦即解释为非真实的。这一判断与“玄学”断言同样傲慢,玄学断言试图超越人类的界限,把我们的心灵状态归因于一个我们无法经验的神。心理主义只不过是玄学冒犯态度的反面,恰恰和后者同样幼稚。但是在我看来,赋予心灵和经验世界以同样的有效性,承认它们具有相同的“实在性”要合理得多。对我来说,心灵是一个世界,自我就包含在这个世界之中。也许还有些鱼相信它们包含了大海。若想从心理学去考察玄学,就必须摆脱这种常见的幻觉。
“金刚体”的概念就是这样一种玄学论断。“金刚体”是在“金华”或“寸田”中产生出来的不能毁灭的气息身体。和诸如此类的其他事物一样,这个身体象征着一个显著的心理事实,由于是客观的,此心理事实首先投射为有机生命体验所提供的形式,即果实、胚胎、婴儿、活体等等。该事实可以最简洁地表达为:并非我在活,是它使我活。对意识占据统治地位的幻觉使我相信:我在活。如果通过承认无意识而打破这种幻觉,无意识就会显现为某种包含着自我的客观的东西。这种对待无意识的态度类似于原始人的感觉,对原始人来说,儿子保证了生命的延续。这种非常典型的感觉甚至可能以一些怪异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老黑人在责骂他不听话的儿子时会大喊:“他的身体是我的,却不听我的话。”
这涉及内心感受的一种转变,它类似于父亲在儿子初生时所体验到的变化。我们从使徒保罗的自白中已经知晓了这种转变,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注41 “基督”作为“人子”的象征是一种类似的心灵体验:一种人形的更高的精神存在不可见地诞生于个体中,这个气息身体(pneumatischer Leib)将为我们提供未来的居所,如保罗所说,就像穿在身上的衣服(“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注42 当然,用理智的概念言说方式去表达对于个体的生命和幸福来说极为重要的微妙感受总是很棘手。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取而代之”(Ersetztsein)的感觉,但并不包含“废除”(Abgesetztsein)之意。此时生命的引导者仿佛托付给了一个无形的中心。尼采的隐喻“在充满爱的强制中自由”(frei im liebevollsten Muss)用到这里很贴切。宗教语言中有大量的比喻性表达可以描述这种自由的依赖性,描述对平静和服从的感受。
在这种值得注意的体验中,我看到了一个因意识的分离而导致的现象,主观的“我在活”由此成为客观的“它使我活”。这种状态被认为要高于之前的状态,就像是从神秘参与所必然带来的强迫和不可能的责任中解脱出来。这种解脱感完全充满了保罗,它是成为神之子的意识,使人从血的魔咒中解脱出来,也是与万事万物和谐一致的感觉,因此《慧命经》说,圆满之人的目光将回到自然之美。
在保罗式的基督象征中,东西方的最高宗教体验相遇了。背负苦难的英雄基督,盛开于玉城紫府的金花——多么强烈的对比!多么不可思议的差异!多么深的历史鸿沟啊!这个问题势必成为未来心理学家的杰作。
除了目前重大的宗教问题,还有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重要问题,那就是宗教精神的进步。如果要谈这个问题,就必须强调东西方对于“珍宝”(Kleinod)这一核心象征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西方强调人的成长,甚至是基督的人格和历史性,而东方则说“不生不灭,无去无来”。基督徒按照西方的观念让自己服从于一个高等的神性人格,期待获得他的恩典;而东方人却认为,解脱全凭自己所下的“功夫”。整个道都从个体中生长出来。效仿基督永远都有一种缺陷:我们崇拜的是一个作为神圣典范的人,他体现了最高的意义,然后出于纯粹的模仿,我们忘记了实现我们自身最高的意义。事实上,放弃一个人自身的意义并非完全令人不快。倘若耶稣这样做了,他可能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木匠,而不会成为宗教叛逆,当然,今天还会发生与之类似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把对基督的效仿理解得更深一些,比如把它当成以耶稣那种勇气和自我牺牲来实现一个人最佳信念的责任,这种信念一直是个人禀赋的完整表达。不得不说,好在并非所有人都肩负着成为人类领导者——或大叛逆——的任务,因此每个人最终都能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这种坦诚甚至可能成为一种理想。巨大的革新总是开始于最不可能的角落,比如今天的人早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自己的裸露感到羞耻,这是认识自己本来面目的开端。接下来还会对以前严格禁忌的许多事物有更多的认识,因为世间现实不会像德尔图良(Tertullian)所说的“少女的面纱”(Virgines Velandae)那样永远隐藏在幕后。脱去道德面具只是沿着同一方向迈进的一步,向前看去,那里站着一个人,他诚实地面对自己,如实地坦白自己。如果他觉得自己这样做毫无意义,那他就是一个不明事理的愚人;但如果他知道自己这样做的意义,他就是更高层次的人,他将不顾一切痛苦来实现基督的象征。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早期宗教阶段非常具体的禁忌或巫术仪式在下一个阶段会成为与心灵有关的东西,甚至是纯精神的象征。在发展过程中,外在的法则会成为内在的信念,于是存在于外在历史空间中的基督很容易成为新教徒内心之中更高的人。这样便以欧洲的方式达到了与东方开悟者相应的心理状态。
所有这些都是一种更高人类的意识朝着未知目标迈进的发展过程中的一步,它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玄学。到目前为止,它总体而言仅仅是“心理学”,但也可以被体验和理解。感谢上帝,它是真实的,具有可操作的实在性,这种实在性包含着预感,因此是活生生的。虽然我只满足于心理上可以体验的东西,拒斥玄学,但任何一个明眼人都会看到,这并不意味着我摆出怀疑论或不可知论的姿态反对信仰,反对相信更高层次的力量;我想说的意思差不多就是康德在把“自在之物”称为一个“纯粹否定的边界概念”(lediglich negativen Grenzbegriff)时所说的意思。每一条关于超验的说法都应当回避,因为它必定只是尚未意识到自身限度的人类精神的可笑僭越。因此,当上帝或道被称为灵魂的一种冲动或状态时,我们所说的仅仅是某种可知的东西,而绝非不可知的东西,对于后者,我们什么也确定不了。
六、结语
我这篇评述的目的是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一座内在心灵理解的桥梁。人是一切真正理解的基础,所以我必须谈及人的事情。因此之故,我只讨论了一般内容,而没有讨论具体技术。对于知道照相机或汽油发动机为何物的人来说,技术指导很有价值;但对于那些对此类设备一无所知的人来说,技术指导毫无用处。而我的写作所面对的西方人正处于这种状况,所以在我看来,强调东西方心灵状态和象征之间的一致性是最重要的,因为凭借这些类比可以开辟一条通往东方精神内在空间的道路。这条道路并不要求牺牲我们自己的本性,不会使我们面临失去依靠的危险,它也不是一架理智的望远镜或显微镜,向我们展示一些与我们没有根本关系、触动不了我们的东西。毋宁说,它是一切文明人所共有的承受、探求和努力的氛围,是自然加诸人类的关于觉醒的巨大实验,它将差异巨大的文化结合成一项共同的任务。
西方的意识绝非普遍意识,而是有着历史地理因素的限制,它只代表人类的一部分。对我们自己意识的拓宽不应以损害其他种类的意识为代价,而是应当发展我们心灵中那些与异域心灵相似的要素,正如东方也不能没有我们的技术、科学和工业一样。欧洲对东方的入侵是一种大规模的暴行,它给我们——位高则任重——留下的责任是理解东方的思想。这项责任也许比我们现在意识到的更加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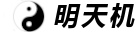 明天机周易网
明天机周易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