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三 譯註《高島易斷》有感
一、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麟少年時,家父在京得到舊本《高島易斷》,一閱傾心,便將其點校刊行,使此易學佳作重行於世,至今深為讀者所喜愛。前年,慮及此書最適於初學者,卻至今仍是古文,家父便有意將其譯為白話,命我從旁助理。麟治《易》,向來被家父笑為未入門,此番便不敢不以勤補拙。猶記當時舉家暫住一毛坯房內,酷暑唯摺扇兩柄而已,麟下班便打起赤膊,與家父並肩揮汗。從譯註至校清成稿,前後近一年。
《高島易斷》雖非文學,在我讀來,卻每每恍如親見高島氏本人。一如其人相片,高島氏神情淡漠,儀態端嚴,行止語默似乎無不古意猶存,一派粹然儒者的氣象。細玩諸爻占例,如同翻閱高島氏日記,可見其人天性沉靜卻每每理想主義,多謀善斷又不失真摯熱忱。時而為國事民生憂患傷懷;時而在燕居中怡然度日;時而以易助人,當機立斷;時而還為故人逝去、美人遲暮悵惘一番。每當占卜奇驗,高島氏的自得之情便躍然紙上,間或慨嘆易道之深邃難盡;偶爾被世俗譏諷,高島氏便漠然以對,不屑多言一字。在舉國傾慕西學的日本明治時代,高島氏毅然以弘揚聖學為己任,富貴已極卻不改初衷,畢生夬夬獨行,至死方休,其精神真足以奮興士人,振起頑冥。至於其人暗懷先人牌位朝見天皇、上疏倡議恢復陰陽寮諸舉,即便在當時,也有幾分迂夫子的可愛與天真。然而,相信在善讀書人眼裡,必能於其可愛處,愈見其人之可敬;於其天真處,愈見其人之不可及。
高島氏之易,雖偶涉納甲、爻辰,然大體宗費氏家法,以《十翼》解經,不疑一字,不贅一語,保有孔門易學之原味。許多讀者為高島氏之奇驗所折服,揣測其人當有不傳之秘,於是熱衷於改易筮法,搜羅占具,或於占筮前持咒祈請、焚香禮拜等等,不知高島氏曾自述在獄中捻紙條代蓍草,晚年亦曾以六枚硬幣一擲成卦,結果始終每占必驗。由此來看,易占應驗與否,與占具關係不大,關鍵在人。
占雖小道,不以精誠貫徹則不能盡其妙,君子十發而一不中,便不敢藉此決疑。占驗之關鍵,人每謂「心誠則靈」,《中庸》言「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高島氏本人亦有「至誠無息」之術。此「誠」字,想來許多人都草率看過,以為占卜時全神貫注、不起雜念之謂。以我淺見,占卜時集中精神雖屬必要,然只此還不足以言誠。依古人定論,誠是人在時時克己修身、充養性德中達到的一種純然無邪之境。《繫辭》揲筮之法,常人頃刻即可學會,然而佔得的結果卻多不應驗。而深於易道之人,蓍草信手中分之際,如同武術家瞬發一手,其快如電光石火,倏忽之間,畢生修為與積澱竟全蘊其中,只此不聞不見之實在功夫,才是常人所不及處。
今人學《易》,以卦爻辭占筮者,千人之中或僅存一二,其餘皆取卦象配天干地支、以五行生殺之類推演。此種技法,精於塔羅者亦不落下風,且生生割斷經文與易占間的聯繫,謂學此即是學《易》,竊謂不可,蓋所失已近於買櫝還珠。
揣度聖人贊《易》之微義,想是春秋時易道大壞,時賢睿士各取伏羲氏卦象立佔法、作爻辭,然其學不見道,故其說各有偏弊,相循即久,徒令學者紛紛爭議,莫知所宗。聖人既竭韋編三絕之功,懼易道湮滅雜說間,見學者或偏好易理,或偏好易占,於是獨取先王卦爻辭,全以人事言天道,配揲筮之法,以卦爻辭主占筮。聖人一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已經說盡自家宗旨。自是,以易理入手者,於體道窮理中便自然熟稔易占,臨事而能斷;以易占入手者,於推玩卦爻辭中便自然親近易理,涵泳其天則。易理、易占於是合一,即理即占,惟義是斷,體用兼備,可相待而長。約其大體言之,可謂審時度勢存乎卦,中正偏倚觀乎位,用剛用柔見乎爻,君子小人判乎辭。易道既備,匹夫匹婦學之皆可怵惕警醒,進德修業以趨於君子。而後世納甲諸法不涉經文,「官鬼」、「妻財」諸辭意極鄙俗,全泯古易風致,其術雖堪前知,卻只知吉與不吉,不知義與不義,捨本逐末,流於術士方技。
前輩每謂麟有家學,必自幼飽讀易書,實則麟讀此類最少,緣其書過多,必有所不讀方堪入手。依慣例,麟見其書有整句翻譯卦爻辭者必廢而不讀,蓋卦爻辭乃聖人天德發縱、自然成文處,唯其虛靈,故能典常。猝然讀之,往往不類完句,然因事而解,一爻可盡天下事。以治經論,解卦爻辭只可推原字詞本意,揆象落實,使聖人之意融會我心,倘整句譯為白話,則經文立化為舉一廢百之死句,不可再以卦爻辭稱。如經文一「貞」字,時取「事之干」義,時取正義,時取固義,時必兼正、固二義方洽,時取漸義,時取斂義,時取守義,時取徹義,不一而足。以斷卦論,則以上諸義皆可取,取冬、北、真、針等義亦不妨,惟操持取捨在人。《易》非文學,務求通順而翻譯潤色之,此門外漢用功處,前賢不取。
學《易》,當折中於聖人,博採於前賢,待心中有所操持,再讀今人書則自極明了。以日喻《易》,聖人論《易》,如直透雲外,但見長天寥廓,烈耀橫空,上下前後,所見皆圓,惜其書不得盡言盡意而已;大賢論《易》,則如履地觀天,或說日在遠山外,或說日在浮雲畔,其說各有不同,然總是實沐其光,真見其灼灼然。今人論《易》,則多如鉛雲四塞,其說多從臆測中得來,故人人皆有新見。
去春麟來京謀職,也翻些手邊易學新作,得見些以易學聞名之人,私以為或有商賈氣,或有術士氣,學究氣者已不多見,更未見有君子沉毅凜冽之氣。學《易》者之眾,歷代未有過於今日者,然其人尋章摘句,裝點門面者有之;滕口滔滔,言不及義者有之;穿鑿附會,自矜創見者有之;一葉障目,廢道論器者有之;皓首窮經,不履一理者有之;自負晚出,睥腉往聖者有之;怪誕形貌,佯狂取寵者有之;妄臆天數,妖言惑眾者有之。謂《易》乃哲書、政書、史書、禮書、兵書、謀書、巫書、咒書者皆不乏其人。嘗見一派斷言《易》乃房中書,問之,曰若干大學者考證,陰陽爻即男女性器所演變。麟作色斥之曰:「見陰陽爻畫即可想見男女私處,不知何物入眼而不是!」其人張惶結舌,不敢正視,蓋良知不泯,本心與此說亦未合。
種種怪誕,不堪盡述,然此輩皆自謂得易學奧蘊,藉此謀食立業,聚徒講學,乃至著書流布者不計其數。與其論理則不予信,觀其占,十發五六中而已。此輩平日無所不至,臨占筮方斂容革面,不驗,則赧然曰蒼天不告。本自欺天,天豈肯應?唯其不告,最是忠告。
今人學《易》者多而得其味者少,病痛雖萬狀,病根卻全在學聖人之《易》而不信聖人之教。不思以克己修身、躬行仁義為實下手處,為求前知而貿然學《易》,於是鮮有不熾其私慾者。讀《詩》而不信聖人,猶得文學;讀《書》而不信聖人,猶得掌故;讀《禮》而不信聖人,猶得儀範;讀《春秋》而不信聖人,猶得信史。唯《易》粹三聖英華,門檻至高,不以道心得之,必以賊心失之。以名利心治《易》,猶習武以欺凌人,縱學得二三小伎倆,非但不堪大用,每每反成其人喪德敗身之甘餌。欲從麟治《易》者,前後亦有數人,麟不敢私此,皆命其先精讀四書以期可言,然其人皆唯唯而退,再無消息。觀高島氏書,每見其人於易理體悟愈深,便對聖人畏服愈堅,理既豁然於心,便畢生汲汲於斯,蓋非躬行不足以為樂。無高島氏之志,而奢求高島氏之術,此種情狀,恆卦九三似之。
伏羲氏無書而立易道,我輩治《易》,用功處亦多在書外。《易》之為書,憑天資與勤勉雖可強入手,然與自家心體總有隔閡,所學可大,然必不能化,終無生機自在處。有志於此道者,於精研經義訓詁、通達人倫物理外,尤須時時充養浩然之氣,自重自愛,使言行不慊於心;體仁集義,使我無一不可示人。久之則能安此,常恍然似有所得,心光發露每如雷震光徹,真有雄壯英邁難自羈勒之感。倘存養使熟,使我大處得化,實處可虛,懷此涉世則時時沛然洒脫,真可謂意之所發,物不能遁,志之所期,力足赴之。徐仲車 [1] 、邵堯夫 [2] 諸前輩臨事不佔而知,火候已在高島氏之上,然亦無他神奇,惟修身得力而已。須知人心非只一團血肉,非只思維知覺,乃天地間發竅至精處,苟瑩徹至極,便是天心,感通宇宙,何假人力?前賢常謂人心多私慾,如明鏡蒙垢,照則失真,其垢蔽深者,雖一炬當前而自不得顯。唯勇施銷磨刮洗之功,則雖星辰之遠、雷電之速亦難逃其照。易占能應,即是此理;占而不應,亦是此理。
治《易》,可謂欲速則不進,欲罷則不能,其難在體道,其樂亦在體道。道不須臾離人,此實理也;不修身立誠無以體之,亦實理也。非只造道、立身、求學、幹事,我輩苟有一志未遂,無不當以修身為吃力最緊處,非此則脊樑不立,成敗得失一任於天,小人故行險以徼幸,惟君子貴修己而自至之。修身之要,見諸群經,《易》統萬事,修身節目亦甚分明。論體用:乾,天性也;既濟,王道也。論功夫:剝、復、無妄、大畜,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也。論手段:震,慎其獨;艮,素其位;豫,率其性;履,盪其私。同學諸君,與聖賢書參看互發,玩味必有所得。
君子學《易》何為?夫《易》者,易也,道之體、理之全、性之純也。約其大體而言,本太極之一理,察萬理之所出,揆三聖之仁心,體天命之所系。自昭明德,純然剛勁,則大本得立;審時知幾,發隱推顯,則仁熟義精;虛靈此心,神明此心,則無往非《易》。任三百八十四種境界萬變紛呈,我自知身處何卦何爻,進退周旋,惟義所在;顛沛造次,各得精彩。君子體道至此,庶幾可以參贊化育,與天地並列為三矣。
昔小程子 [3] 《易傳》著成,年逾七旬尚不示人,自言覬有少進。前輩治學之嚴,麟每念之,輒覺傾倒。自顧年未三十一小職員,流蕩散漫之徒,不揣德才俱淺,冒昧繁言,真覺有芒在背。然潔靜精微之道,為今人褻玩一至於此,麟於情有不得不發處,於理亦有不敢不發處,索性藉新編付梓之際,於此書理路稍作發明,自謂雖失之狂狷,未失之鄉愿。既已擱筆,長夜復寂,唯細雪繞屋不止。麟獨處寒室,不覺正坐,意難平復,似有所未盡者。
二、從姤卦九三一個占例說起
姤卦九三占例,即三浦中將奉命為朝鮮公使,臨行占問對朝外交政策一卦,竊怪高島氏語焉不詳,似有所諱。檢之史冊,與本占例直接相應者,更似三浦梧樓赴朝鮮刺殺閔妃,即明成皇后一事。
姤者,遇也。象三浦身為公使,得以與閔妃相過從。「姤」又可拆作「女」、「後」二字,閔妃生前垂簾聽政,逝後被追封為後,由此亦見端倪。
彖辭「女壯,勿用取女」,就日方而言,指初爻所象之閔妃陰居陽位,雖未成氣候,然上剝之勢昭然,日本政府忌諱其人攝政之能,見一陰始發於下,必欲除之後快。
《大象》曰:「天下有風,姤,後以施命誥四方。」史載閔妃頗有政治才幹,大權在握,能發號施令,而三浦行刺系受命行,由此亦可見。
三浦於高島處所佔得之姤三爻,本已過剛不中,又居巽體之末,巽究為躁卦,可謂剛惡險暴已極。「臀無膚」,言其乘渡輪遠涉重洋;「其行次且」,言其謀劃周密,不敢妄動。「厲」,言其鋌而行兇;「無大咎」,言其暴行雖可誅,然幕後有日本政府及頭山滿斡旋撐腰,故能免責。
統觀全卦,外卦乾為武人,象三浦,內卦巽為長女,象閔妃,外內有乾金克巽木之象。三爻變,則內卦化坎,坎為盜寇,為血卦,有偷襲之象。三爻變,則初爻之上現一離卦,離為火,與事變後以煤油焚燒閔妃屍體相應。倒卦為夬,夬者決也,「揚於王庭,孚號有厲」也,此為暴徒突襲王宮,宮人奔走呼號之象。
此爻變,則化為訟三爻,訟三爻曰:「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此案發生後,朝日兩國輿論爭訟不已,歐亞諸國皆深表關注,三浦亦被起訴,然因其人於日帝國有鷹犬之勞,終以證據不足為由獲釋,此為「食舊德,貞厲,終吉。」其後,三浦仍積極為政府出謀劃策,然淡出公眾視野,暗居幕後,是為「或從王事,無成。」
卦象爻辭與史實若合符節,竊謂高島氏此占或有斷卦未精之失,或有避重就輕之嫌。然而編撰《易斷》之時,此例大可不錄,置於《易斷》流傳後世,莫非亦怕真相終不得彰顯?
縱觀高島氏一生行徑,可謂志士楷模,惜其人不免當時軍國思想,未可輕許以仁。且儒者多為一時尊長者隱,如涉及本國政治之例,高島氏從未對五爻君位有所指摘,讀者宜注意。
白璧呈前,瑜瑕自不相掩。斯人已逝,斯編在手,是非功過全在讀者心中,倘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高島氏有知,想來也會欣然首肯。
孫奧麟於北京北宮門寓
注釋
[1].徐仲車:名積,北宋聾人教官。楚州山陽(今江蘇淮安)人。性至孝。初從胡瑗學,治平四年進士,以耳聾不能仕。元佑初近臣交薦其孝廉文學,乃以揚州司戶參軍、楚州教授,轉和州防禦推官,改宣德郎。賜謚節孝處士。《宋史》有傳。
[2].邵堯夫:名雍,謚康節,自號安樂先生。北宋哲學家、易學家,有內聖外王之譽。其先范陽(今河北涿縣)人,幼隨父遷共城(今河南輝縣)。少有志,讀書蘇門山百源上。仁宗嘉祐及神宗熙寧中,先後被召授官,皆不赴。創「先天學」,以為萬物皆由「太極」演化而成。著有《觀物篇》、《先天圖》、《伊川擊壤集》、《皇極經世》等。
[3].小程子:指程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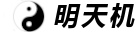 明天機周易網
明天機周易網












